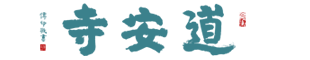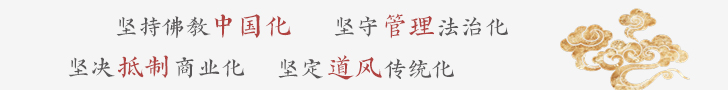善默能語 一默如雷
當西方語言哲學強調語言是與客觀事物一一對應之時,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卻充分看到了語言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在言語之外,他更關注的是“沉默”,甚至認為沉默才是意識表達的“本體”,而語言不過是沉默的一個瞬間,相比於口若懸河與滔滔不絕,沉默反而是一種更高級、更本質、也更直接的“語言形式”,因為真理在語言盡處。
不惟如此,在中國思想文化中,古聖先賢對於“言說”與“沉默”的辯證關係有着更深刻的認識:“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大辯若訥”(《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游》)、“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莊子·寓言》)、“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周易·繫辭下傳》)等等的記載不一而足。

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手拈金婆羅花,在大眾默然,迦葉微笑之間,完成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的心傳,成為禪門第一公案;而“維摩現疾、文殊問疾”更是成就了“一默如雷”的佛門佳話。

佛陀在毗耶離城庵羅樹園為大眾說法時,居於城中的維摩詰居士示現身疾,佛陀深知其意,先後徵詢舍利弗、大迦葉、須菩提等諸大弟子前往問疾,然卻都言“不堪任詣彼問疾”。最後佛陀委派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率眾前往探視,於是在維摩丈室內大家有了一番關於“入不二法門”真實法義的深入探討。在文殊菩薩做了“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的總結髮言後,反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以“默然無言”相對,文殊菩薩不禁讚歎“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說空說有,仍落言筌;維摩一默,聲如鳴雷。宇宙的實相此刻就在維摩居士的沉默之中。

爾後禪宗大行於東土,在祖師接引學人的公案中更是常見“沉默”方法的使用,不僅有“默然”、“不語”、“良久”這類溫和的形式,同時也會通過“當頭棒喝”這樣看起來比較極端的方式行“無言”之教。

明代馮夢龍所著《智囊》中載有一則“藝祖屈徐鉉”的故事。
南唐後主李煜派遣博學多才、名著江左的徐鉉來宋朝修貢,依例朝廷要差官押伴、隨侍左右。但因為徐鉉的學問和名望太大了,朝臣們都擔心自己口才詞令不及,宰輔一時也不知安排何人來應對。太祖趙匡胤見此情形,便親自從殿前司的禁衛軍中挑選了一名目不識丁的侍衛來擔此任。雖然不解太祖何意,但中書也不敢再問,便匆匆催促這名侍衛前去和徐鉉會和,就連侍衛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見面之後,起初徐鉉口若懸河、詞鋒如雲,眾人都驚愕不已。但這名侍衛因實在無以應對,只有不發一言、唯唯諾諾點頭應答而已。徐鉉也摸不清這位使者的水平深淺,只好硬着頭皮繼續高談闊論。就這樣一連好幾天,這位使者和徐鉉之間都沒有任何的酬答應對,徐鉉因此也把自己搞的很疲憊,於是也就沉默不語了。
其實當時大宋在朝的明儒碩學比比皆是,如果派他們去“角辯騁詞”難道就會不如徐鉉么?在該段評論中認為是“藝祖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所以採取了這樣一個“以愚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該段軼事所講雖然不盡如“世尊拈花”、“維摩一默”那樣內涵深邃,但也無妨從另一側面對“善默即是能語”來做註腳。
無論形上形下,其實從所想到所說,便早已有了距離,言語本身的特徵決定了它的局限性。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恰如繪畫里的留白、詩詞中的餘韻反而擁有着無限的可能,更解“善默能語”真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