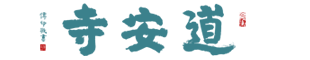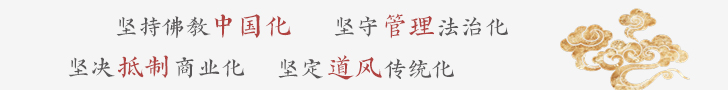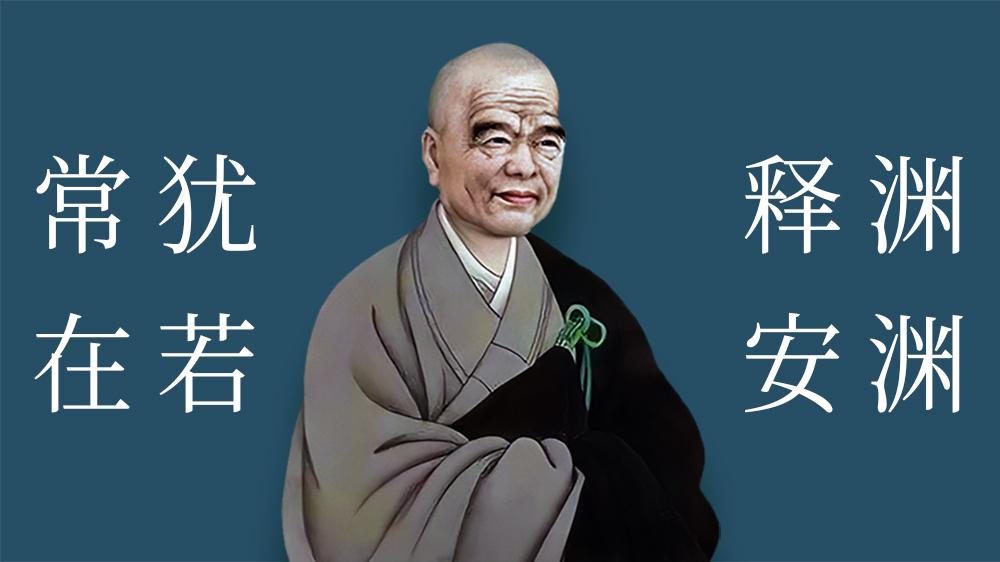道安大師對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貢獻
佛教傳入中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本土化過程,在這一進程中,諸多高僧大德功績卓著,道安大師無疑是其中之一。道安(312-385),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東晉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事業,注重佛教教育的推廣、普及和發展,對中國內地佛教僧團的建立和中國佛教理論體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湯用彤稱“釋道安法師之德望功績,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樹,比之同時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猶若常在也。”

中國佛教的發生是以佛經的譯介與推廣為先導,因而在中國佛教早期發展中,佛經譯介的準確性顯得尤為重要。東晉時期佛典漢譯尚處於無序狀態,譯本質量參差不齊,輾轉傳抄中以訛傳訛的現象非常嚴重。道安法師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雖因不通梵文而沒有翻譯佛經,但對佛教翻譯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思想。
“五失本”(五種譯經中的失誤)涉及到譯經中的語序、文質、詳簡、思維等問題,“三不易”(三個譯經中很難做好的方面)涉及到翻譯面臨的時代因素、讀者因素和譯者因素。道安法師在此問題上的觀點如何,因資料不足,學界還有不少的爭議,但他對佛經翻譯上的貢獻卻世所公認,為當時大規模譯場翻譯的有序進行奠定了基礎。錢鍾書先生對此評價頗高:“論‘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國翻譯術開宗明義,首推此篇。”釋彥琮在《辯證論》中完整地引用了道安法師的“五失本、三不易”內容,認為其“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梁啟超在論及“五失本、三不易”時指出:“後世談譯學者,咸徵引焉。要之翻譯文學程式,成為學界一問題,自安公始也。”
此外,道安法師還對佛典漢譯的譯者和譯出年代嚴加考證,整理編撰了《綜理眾經目錄》,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佛典目錄,收錄了東漢至東晉兩百年間的佛典譯本與注釋作品,開創了佛教史和翻譯史上目錄學的先河,為整理佛典譯本,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僧寶作為佛教三寶之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僧團建設成為佛教發展中極為關鍵的一環。魏晉是佛教在中國社會逐漸立足並壯大的時期,佛教在與中國本土思想和文化習俗的調適中,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僧團體制,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佛圖澄僧團、道安僧團、鳩摩羅什僧團、慧遠僧團等。僧團的出現,有利於佛教的本土化和制度化,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道安法師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舉措功不可沒。
第一,以“釋”為姓,統一中國佛門。漢魏以來,中國佛教徒姓氏甚是紛雜,西域僧人依持本姓,如安、支、康、竺等;中國出家僧人皆依本姓,或取胡音、師姓。這一方面對中國佛教之一體化發展極為不利,另一方面,對於消彌僧團中僧眾出身的階級差別及僧團的現實差別,進而將僧團導入統一化發展也產生了很大阻礙。因此,道安法師獨出心裁,以佛教“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此“遂為永式”。佛教僧尼之以“釋”為姓,從而減少了由於姓氏上所表現出的國家、民族、階級、門第差別,強化了宗教統一的色彩,對中國佛教不同地區、不同宗派的融合與一體化發展以及中國佛教僧團的統一意義非常大。
第二,為僧尼定軌範,制定中國化的僧團制度。道安僧團的內部組織管理主要依持佛制戒律。道安法師特別重視戒律,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但其時佛教戒律相當不完備,因此道安法師在佛教戒律的譯傳方面頗多用心。他感到僧團戒律與組織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極大地制約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意識到了完善戒律等僧團組織管理制度的迫切性。於是他一方面努力搜求與組織翻譯戒律;另一方面還參照現有的並不太完備的戒律制定了中國佛教僧團的“僧尼軌範”,成為中國佛教制定中國化的寺院僧團組織管理制度的重要嘗試。
第三,廣布徒眾,遍播佛種,為中國佛教建構信眾之基石。道安法師提出了“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的名言。這既深刻地總結了外來佛教傳入中土後生存的路數,又指明了佛教得以在中國傳播、發展並不斷壯大所要遵循的弘法新思路。道安法師“家世英儒”,尚未出家前就閱讀了很多儒家文籍,他作出如此精闢的總結也是基於對中國文化及綱常倫理的了解和在佛教傳入中國前所形成的以儒家為主體的思想體系的認識。
總之,道安僧團在東晉時期規模極其宏大,社會評價很高。習鑿齒在《致謝安書》中稱讚道:“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大威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隨着道安法師聲名的遠播,“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僧團規模隨之擴大,社會影響越來越廣。

在佛教義理上,道安法師對般若學做了玄學化的詮釋,並依此開創“六家七宗”中的本無宗。般若類經典在東漢時就己傳入中國,到西晉,它藉助玄學術語流行。三國時,支謙仍然沿用“本無”對譯“真如”,朱士行譯《放光般若經》、西晉竺法護譯《光贊般若經》,都沿用了格義方法,東晉之初,在士大夫階層中更蔚然成風。佛教學者自由闡發對“空”的理解,從而形成六家七宗的不同學說。在六家七宗中,最主要有三派:一是本無說,認為無(空)為萬化之始,萬物之本;二是即色說,主張“即色是空”,物質現象本身就是空的;三是心無說,強調主觀的心不能執着外物,外物不一定是空無的。這些學說的共同特點是以“無”解“空”,這三派正好和玄學的貴無、崇有、獨化三大派很接近,即何晏、王弼等主張的“貴無”論;裴頒提出的“崇有”論;向秀、郭象提出的“獨化”論,這些流派構成魏晉玄學的主要傾向。當時玄學名士與佛學名僧交往,名士以玄學談論佛理,名僧以佛理髮揮三玄,形成魏晉時期玄佛合流的思潮。
道安法師的般若學就在玄佛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展開。道安法師的般若思想以“本無”為宗,以魏晉玄學的本末體用思維方式來理解般若經,他把“如”、“法身”視為根本本體,是不適合印度佛教本義的。般若經提倡空觀,破除現象和本體的實有,否定本體存在,或者說主張本體是空。而道安法師則提倡“以無為本”,把破除本體實有的般若經改造為本體的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說,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印度佛教哲學的方向,改造了印度佛教哲學的內容,構成具有中國特色佛教的本體論。曇濟《六家七宗論》說道安法師是“本無宗”的代表,吉藏《中觀論疏》更清楚解釋道安法師的本無宗,陳慧達認為僧肇所破本無義即指道安、慧遠的思想,僧肇認為道安的“本無”與方等經並論,梁武帝《大品經序》也以道安、羅什並美。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至道安法師所處之時期,幾近四百年。這一漫長的過程,是佛教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明相互融合的關鍵時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的關鍵時期,是由依附而逐漸走上獨立發展之路的時期。期間,道安法師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對佛教中國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王權與政治的關係上,道安法師以其深遠卓識,提出“不依國主,法事難立”的觀點,通過佛教與政權的密切結合,依靠政權的力量,促進佛教的發展與傳播。同時,在僧伽組織方面,統一姓氏為“釋”,加強其內部的凝聚力;重視佛教戒律與僧團儀軌的建設,提升組織性與紀律性,為僧人提供一種有序的修持儀軌,為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佛教義理方面,道安法師法師頗有其理論建樹。佛教初傳入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依附很大,因此無論是在佛經翻譯還是在義理弘傳諸層面,都深深的染上了傳統思想的印記,佛教“格義”即是鮮明的代表。但是佛教“格義”在促進佛教與傳統文化融合的同時,亦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病,即不能正確理解佛教義理,從長遠發展來看,無疑是不利的。道安法師在研究佛教義理過程中鮮明的感受到了這一點,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不局限於固有師說,對此加以反對。雖終其一生未能擺脫格義的影響,但此觀點之提出無疑是當頭棒喝,對此後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道安法師之禪學,秉承其師佛圖澄一系,所傳為有部之禪法。道安法師之般若學理論探討,為當時六家七宗之一,並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家,對當時盛行的般若學研究,及對般若學在中國的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
(選自《第四屆三禪會議論文集(上)——道安法師研究》,文章有刪改。原作者為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習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