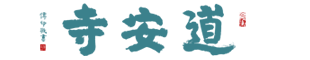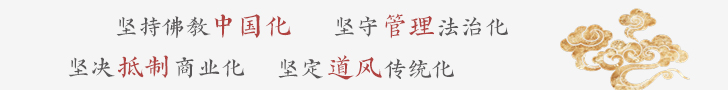靜靜地,等一個人來
我家住邢台,小區緊臨邢台大開元寺。周末閑暇時,常去寺里靜坐。幾位文友在寺里時常搞些文藝活動,或講課,或書畫,或讀書,若無雅興,何來生活情趣?
一次,大開元寺寺院住持明憨法師對我說:“你去衡水工作了,有機會一定要去道安寺看一看。”奈何事務纏身,因緣未到,一直未能成行。不想,前幾天到冀州一次採風時,當地臨時加了一個點位,就是道安寺。
道安,是常山扶柳縣人,也就是今天的冀州區。他生於一個讀書人家。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死於戰禍,被親戚收養。7歲時,他開始習學《詩》《書》,書讀兩遍即可背誦。11歲那年,瘟疫流行,孔氏一家遭遇不幸。道安失去依靠,四處飄泊。據《高僧傳》記載,道安“年十二出家”,投身佛門。
早先,我在冀州博覽館聆聽過道安法師的故事,讚歎冀州不愧為九州之首,真乃聖人之地也。當時記住了一句話:道安,讓天下僧眾有了自己的姓,也就是“釋”,又因其最早對佛教傳入漢地的經典組織翻譯、整理、辨偽、註疏,被尊為“東方聖人”,可以說道安大師是從冀州走出的一位聲震寰宇的高僧。

道安故里,釋姓祖源。道安寺雖是一座新建的寺院,但因坐落冀州,尤為殊勝。走進寺院,綠樹青草,幾許清涼。站在大雄寶殿里,聖道師父為初來此地的我們講起寺院的興建過程,只見十條經幡莊嚴佛堂,兩邊經幢上有經文《楞嚴咒》,都是蘇州手綉,恭敬用心無以言表。大殿通透、敞亮,卻並非坐北朝南,頂部四周窗戶打通,讓自然光線流入大殿,也因此,無論朝陽、夕陽,三尊金色大佛皆可普照光明。
特別是殿內的五百羅漢,姿態各異,栩栩如生,他們或坐或立,或喜或怒,或沉思或談笑,每一尊都有着自己獨特的故事。師父說,塑像的工匠都是來自甘肅天水的80後、90後匠人,當時正值疫情,無緣外出,匠人們在寺院同吃同住,懷揣極其恭敬用心,以細膩的手法,將羅漢們的神態和氣質刻畫得淋漓盡致。有的羅漢面容慈祥,眼神中透露出慈悲與溫和;有的羅漢則神情嚴肅,似乎在沉思着宇宙的奧秘;還有的羅漢面帶微笑,彷彿在與你分享着生活中的點滴歡樂。
值得一提的是,泥塑使用的土是當地的土,部分泥胎里的筋骨是道安寺內的蘆草,就地取材,更顯莊重、和諧。此外,冀州及周邊大眾為成就道場的建設,盡己所能,捐款捐物,正是有這樣眾多護法居士的發心,齊心協力、眾緣和合才成就這佛像的鑄造。

五百羅漢里,道安法師端坐其中。這是一位智者,靜坐常思,又似乎對來人默默地講述着關於人生、關於修行的道理。據說,道安的膚色比較黝黑,佛圖澄弟子稱他為“漆道人”。佛圖澄說:“此人有遠見卓識,你們這些人難與他相比。”講經時,佛圖澄讓道安作複述,眾僧不服,待道安復講時,他們紛紛提出許多疑難,結果道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四座震驚,時有“漆道人,驚四鄰”之美譽。
行游恆山期間,道安大師名聲遠播,來向他學習的人絡繹不絕,遂建立起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龐大的僧團,計有四、五百人。武邑太守盧歆,聽聞道安大師道高學博,派沙門敏見苦苦邀請,道安大師遂下山講經。當時武邑屬冀州,離道安大師家鄉扶柳不遠。道安大師在這裡講經,與其名聲完全相符,這樣一來追隨他的人更多了。之後幾年,北方戰亂,冀州連年災荒,道安最終決定離開北方南投襄陽。

生於河北、長於河北、出家於河北、學道於河北、聲名遠播於河北、建寺立塔於河北、授徒傳道於河北、在圓寂前以七十多歲高齡千里跋涉來探望的是河北,可以說河北是道安法師一生的牽掛。道安寺建於冀州,個中機緣,非簡單文字所能描述。
於城市的邊緣,靜卧一座安寧的寺院,它仿若一位遺世獨立的隱士,隱匿於塵世的喧囂之外。道安寺的鐘聲悠悠響起,這鐘聲彷彿是來自遠方的召喚,喚醒着人們內心深處的良知與善念。在這鐘聲的餘韻中,我緩緩地走出道安寺,與聖道師父作別。然冥冥之中,似與道安法師有了一面之緣。
鐘聲在空氣中緩緩擴散,與衡水湖畔的微風交織在一起,鳥鳴湖城,恍若在訴說著道安的故事,那些關於慈悲、關於寬容、關於救贖的故事。

靜靜地,等一個人來。
隨着最後一聲鐘聲的餘音漸次消散,整個寺院再度恢復了往昔的平靜。然而,那鐘聲,卻永遠烙印在了我的心間,化作了心靈深處溫暖的記憶。
(文章作者:邢雲,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邢雲”)